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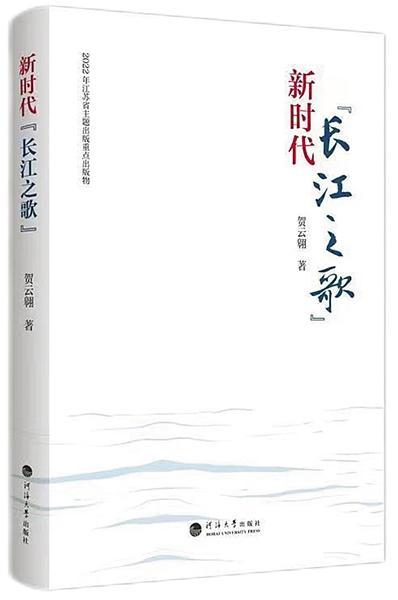
湖北日報全媒記者 王晶 通訊員 余嫚雪
國慶節前,長江文化藝術季“書香長江”的重點活動長江講壇在湖北省圖書館舉行,南京大學文化與自然遺產研究所所長賀云翱教授主講《長江文化保護性傳承與創新發展》。作為國內最早關注長江文化的學者之一,賀云翱與讀者們分享:創造與革新的基因傳承在長江流域。
舊石器時代、新石器時代、青銅時代,這里的先民們就具有創造性和創新性。賀云翱指出,長江流域是中華農業文明即“農業革命”起源階段的重要一極,是“城市革命”最初發生地,是中華“國家”文明最早誕生的地方。近代工業文明的開創,一直到新文化運動,到紅色文化的誕生,都首先出現在長江流域。改革開放以來,長江流域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及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實踐的戰略性、引領性區域。
大河灌溉出沒有斷代的文明
作為歷史學家,賀云翱首先給讀者們展示了與長江有關的地圖。長江從西到東穿越青藏高原、橫斷山區、云貴高原、四川盆地、江漢平原、長江中下游平原等幾大地理單元,全域河網密集,擁有岷江、沱江、嘉陵江、漢江、湘江、贛江等眾多支流,沿著長江還有洞庭湖、鄱陽湖、巢湖、太湖等重要湖泊。長江貫通名川大湖,形成一個十分巨大的自然與人文區域。
大河孕育文明。賀云翱表示,四大文明古國皆在大河之畔,中華文明進程得以未曾中斷,地理和“天道”的答案首先在于河流。從地圖上看,尼羅河、兩河(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)、印度河與恒河,它們基本是南北流向,而長江與黃河是東西流向。由于地球運動和太陽運動的相互關系,深刻影響到大地不同經緯度所經區域的氣候及水熱條件,南北流向的大河及其流域對于物產的孕育及人文的分布,受光照與氣候的影響而產生很大差異,容易導致文明的分解,相對而言,東西流向的河流對于物產的孕育是恒定充足的,相對統一的自然板塊也能夠成就巨大的文明板塊。長江大約在北緯30度至32度之間,流域絕大部分處于水熱資源配合良好的濕潤地區,從而形成深厚的長江文明板塊。黃河流經北緯40度線左右的黃金種植和游牧地帶,也形成了巨型的黃河文明板塊。長江與黃河緯度不同、氣候不同,導致了農業及其他文化特質的不同,兩者形成了互補和支撐,從物質層面保障了中華文明的持續生存與發展。
長江文化的宏闊氣象,離不開千萬年的深厚積淀。賀云翱為讀者們從時間維度做了梳理:
——長江流域發現過約200萬年前左右的龍骨坡遺址及“巫山人”化石、安徽繁昌“人字洞”石器、170萬年前的云南“元謀人”化石等。從直立人到智人化石,長江流域都有發現,序列清晰。
——數千年前,長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下游的良渚文化交相輝映。
——兩周之際,形成巴蜀、荊楚和吳越三大文化圈。
——至秦漢時,楚文化參與了統一國家建構,南北區域的共同發展推動長江文化在不斷交流中取長補短,奠定了其規模和內核。
——經過魏晉南北朝、隋唐時代、宋室南遷的歷史人口和文化變遷,我國經濟重心逐漸轉移,文化資源持續向南方集聚,海上絲綢之路溝通中外,確立了長江文化在整個中華文化版圖中的重要地位。
——明清兩代長江文化臻于繁盛。步入近代,工商文化成為長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從原始石器文化到現代工商文化一脈相承,長江文化記錄了中華文化的一次次巨變和連續發展,從而結出燦爛的文明碩果。
從空間跨度看,長江流經11個省區市,青藏地區的羌藏文化、長江上游的巴蜀文化、長江中游的楚文化、長江下游的吳越文化等,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交匯融合、互聯互補,最終匯集為兼容并蓄、意蘊深厚、氣勢磅礴的長江文化,形成了一條獨具特色、融會貫通的文化聚集帶。可以說,長江文化是一個時空交織的多層次、多維度的文化復合體。
武漢商代盤龍城遺址是“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的結合點”
歷史發展到5000年前左右,世界上幾個大河流域都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國家文明。在今天的中國境內,最早的國家文明出現于長江流域。2019年成功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良渚文化古城遺址正是5000年前良渚文明誕生的標志性遺存。
大約在4000多年前,中國的文明中心在黃河中游地區,以夏王朝的出現為標志。進入商王朝時期,長江流域的經濟文化地位重新崛起。整個青銅時代,長江流域因盛產銅、錫原料而受到中原王朝的高度重視,賀云翱舉例說道,處于武漢郊區的商代盤龍城遺址是與中原王朝控制長江流域銅、錫資源有關的重要遺存,是“黃河文化與長江文化的結合點”。
秦的統一,使得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一體化發展,共同成為華夏文明中的核心內容。“楚人”劉邦建立西漢王朝,漢語、漢字、漢賦、漢民族、漢文化、漢文明等等都因“漢水”上游的“漢中”及西漢而得名,而漢文化體系中更是包容著大量楚文化要素。西漢初年“無為而治”的治國理念就源自誕生于楚地的道家思想。
長江流域攀登上更高的文化高峰是從漢唐之間的六朝時代開始的。三國、兩晉、南北朝,多次戰亂,長江成為阻擋北方胡馬南下,保護中原百萬南渡人士及江南土著民族的一道天險,黃河流域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江南大地得以保存和發展。晉元帝說過:“今之會稽,昔之關中”,把浙東平原一帶比喻為曾是膏腴之地的周漢立都之地關中沃野。廣州出土東晉磚銘也有“永嘉世,天下災,但江南,皆康平……余吳土,盛且豐”的記載。
隋唐統一和秦漢統一最大的不同,就是長江流域的全面崛起,唐代人有謂長江下游區域是“繭稅魚鹽,衣食半天下”“天下大計,仰于東南”之勝地。韓愈則說“當今賦稅出天下,江南居十九”即占有十分之九的地位。到唐代中葉,“安史之亂”之后長江流域經濟文化地位超過黃河流域的格局便大體定型。
據國內外史家研究,兩宋時代商品經濟、文化教育、科學創新均達到中國古代最繁榮的時期。咸平三年(公元1000年),中國GDP總量折算為265.5億美元,占世界經濟總量的22.7%,人均GDP達450美元,超過當時西歐的人均400美元,民間經濟之富庶繁榮程度遠超盛唐,故而大史家陳寅恪先生說“華夏民族之文化,歷數千載之演進,造極于趙宋之世”。
兩宋之際,中原人口第三次大規模南下,中國經濟中心也徹底轉移到長江一線,尤其是長江下游地區成為全國最富庶之地,南宋時期形成了“上有天堂,下有蘇杭”之說。
元代的長江流域,棉種植業和棉紡業都堪稱發達,景德鎮成為中國及世界的“瓷都”。明朝的建立,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以南京及長江流域為中心完成統一全國的任務。此時的南京成為海上絲路的中心城市,在這里,鄭和七下西洋,28年間航行世界30余國,把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推到了歷史的巔峰。明末,漢口號稱“楚中第一繁盛處”,又有“九省通衢”的美譽。
長江流域既是標志著中國進入近代史的《南京條約》的簽訂地,也是被動接受這種“挑戰”并率先做出積極探索的區域。近代史上幾乎所有重大的里程碑事件都發生在長江一線。
經濟繁盛背后隱藏著文化的發達和思想的創新
文化是人的本質,而文化的核心是人的精神文化,一切創新都是以人的“精神文化”創新為先導。明清時代,長江流域已經是人才淵藪。位于南京的國子監,一度學生規模達到9000多人;“江南貢院”作為長江下游科舉重地,走出過大批的封建國家治國人才;蘇州則成為“狀元之鄉”。
美國學者馬麥可認為,15—18世紀,蘇州儒、商結合的社會精英分子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文化上的獨特創造能力,他們能通過詩禮傳家、科舉考試等途徑,一代一代形成良性循環,從而影響整個江南乃至明代中國。
賀云翱解讀,從更大的范圍而言,明清時代,長江流域整體上處于全國經濟的高位,其背后隱藏的是文化的發達和思想的創新。如在長江下游,以南京、杭州、蘇州、徽州、紹興等城市為中心,形成了一個江南文化圈,由教育、思想、科舉、出版、藏書、學術、手工技藝、園林建筑、書畫藝術、文學創作、戲曲、宗教等文化要素組成,這一文化圈代表了中國古代社會的又一文化高峰,許多文化成就一直影響到清代乃至近現代。
在長江流域,明清時代產生過大量優秀學術成果,如王陽明的心學,王艮的泰州學派,無錫的東林之學,以顧炎武為代表的實學,王夫之的啟蒙之學,乾嘉學派中的吳派、皖派和揚州學派,常州學派,安徽的桐城派,湖南的湖湘學派等。其中湖湘學派起于兩宋,到明末清初以船山先生為代表,形成名家層出的態勢,從曾國藩、左宗棠、郭嵩燾、魏源、陶澍、賀長齡到譚嗣同、陳天華、黃興等,展現了該學派經世務實、愛國體民的優良傳統。
諸多講求實學的著作在長江流域誕生,代表作有《農政全書》《天工開物》《本草綱目》《徐霞客游記》《景德鎮陶錄》《陽羨茗壺系》《物理小識》《古今歷法通考》《補農書》《加減乘除釋》《海國圖志》等,許多優秀文化也隨之積累和傳播。
賀云翱說,一個區域,如果只有經濟,沒有文化,其經濟也不可能持久,只有讓經濟與文化互相促進,螺旋上升,才能保證社會的良性發展,而明清時代的長江流域正體現出這種態勢。
賀云翱表示,今天,在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進程中,長江又肩負起新的偉大使命。從“三峽工程”到“南水北調”,從“長江經濟帶”到“長江國家文化公園”,從“一帶一路”交匯地到“生態文明”先行區,從“新質生產力”到“中國式現代化”,既要共抓大保護,不搞大開發,又要創新發展不止步,引領全國作貢獻。這就是長江和長江文化的現代使命。
Copyright ? 2001-2025 湖北荊楚網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
互聯網新聞信息許可證 42120170001 -
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 鄂B2-20231273 -
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許可證(鄂)字第000號
信息網絡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 1706144 -
互聯網出版許可證 (鄂)字3號 -
營業執照
鄂ICP備 13000573號-1  鄂公網安備 42010602000206號
鄂公網安備 42010602000206號
版權為 荊楚網 www.cnhubei.com 所有 未經同意不得復制或鏡像